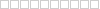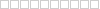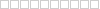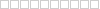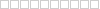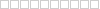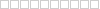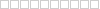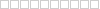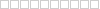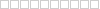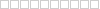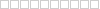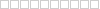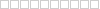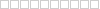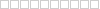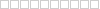对万千中小型个体商人来说,这是一场走钢丝的战争,走不走结局有可能是一样的,但往前走才有可能闯关成功。大部分人愿意这样相信,文伟是其中一个。在他们生意圈子有一个说法:人一旦倒下去了,就很难再翻身了。
在广州琶洲站地铁口,一条1米宽的红毯在地面上铺展开来,上面有荧光绿的箭头,指向前方200米的家居展。红毯两边立着巨大的一面人墙,年轻人们穿着统一的白T恤,举着招揽人群的广告牌。汩汩人潮被动地流入这道人墙,但很快开始分叉,走向不同方向。从人墙中流出来了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红毯的反方向——名气更大的“建筑装饰博览会”。这是疫情以来广交会举办的第一个线下展会。7月8日到7月11日,有将近2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。最开始两天,光是进入展会,就需要走路排队近30分钟。不过,今年的参展商大大缩水,只来了1000多家,展览中心集中在B区,都没塞满。要放在往常,从早到晚,广交会的ABC三个展区都会水泄不通。对着地铁口开了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娘摇了摇头——她已经在这店铺里枯坐半年了,今年此前所有的展会,全是在线上举行。因此,在线下开展第一天,她6点就来到了店铺,烧了10瓶热水,以备有顾客要泡泡面。她原以为这会是鸡飞狗跳的一天,所以提前雇我来帮工。但到中午12点,热水壶只空了2个。店门口垒到天花板的箱装水,高度几乎毫无变化。“生意大不如前,店租都交不起了。”老板娘叹了一句。但这对于刚刚“云毕业”的我来说,是一份不错的兼职,比起外面举着牌子暴晒一天的“人墙宣传工”和老冰棍小贩,我起码有瓦遮头,有扇送风。工资一天180元,不光是他们的两倍,还有冰水任喝。我被老板娘分配在角落卖杂货、泡面以及一些易携带的速食。人们神色匆匆,大多成群结队而来。忙起来时,我也有些晕头转向。但我记价格、物品位置记得快,手脚勤快,开朗话多,老板娘对我还算满意。中午2点,熬过了饭点,人流稍微少了一些。店铺进来一个个子不高、敦实的男人,他穿着橄榄绿的暗色上衣,汗流浃背,想要买水。 我取来水,“3元”。他掏出两部手机,来回扫码,无奈人太多,网络延迟了很久。他又要了一包纸巾,擦拭几乎完全汗湿了衣领的脖子和脸庞。等他手机反应的期间,老板娘问了一句:“老板来看展呢?第一次来?”“对,来看展。”他说话不紧不慢,“我来这个展10年了。”“太难了。”他干笑了两声,“我的生意缩减了九成。”老板娘有些同情地点点头:“唉,今年,大家都不好过。我光烟就在家里囤了十几箱了。”“展厅缩小,展品减少,展商也少。以往展品很多元也很丰富,今年连以往的一些钉子户展商也没有来。”他有些失落,“我这个品类的市场份额被瓜分严重,现在厂家都大多靠电商、直播来直销。连传统的吊顶都开始做定制了,但像定制这样的东西在展会上基本上没看见。”说着说着,他笑容消失了,“业务越来越难开拓了。”他一连串专业、沉着的解读,给了我们一点奇异感。看他矮壮黝黑的身板,朴素的打扮,不太像一个生意人,倒有些像是布置展会的工头。见他手机的网络似乎比一般人的状况还要差,老板娘便招呼他在店铺角落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了。他一边找信号,一边自我介绍,他叫文伟,85年生,江苏人。他身上有一种礼貌和大度,是属于商人的,但那份平和近人,又像是属于工人的。两个人对各自省份的消费水平和工作机会的情况寒暄了一阵后,嘀嗒一声,老板娘收到款了。文伟晃了晃手机,正要起步离开时,一个电话打了进来,他平和的脸一瞬间凝重阴郁起来,零零星星只听到几句:“去医院了吗?”“骨头伤着了吗?”“好,先带他去赶紧缝起来。”他返回来请求坐下,并且用手机飞速处理起事情来。他说,在家乡的大哥在使用卷布机时把手绞进去了,骨头全断了,伤口勉强还沾着皮。“生活总是坏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。”他叹了一口长气。在最初的慌张过后,他又恢复了波澜不惊,做出了冷静的判断:“能接回去,只不过恢复不了原来的灵活度,以后可能也没法正常工作了。”他苦笑,像听见什么好笑的事一样:“没事,家里一直靠我。”听完这个意外,我倒吸一口气。他看我这样子,回忆道:“我2003年在东莞的小工厂,无名指也这样被整个削断了,小拇指骨折。”我忍不住看了看他正安然举着手机的手。他的手指短粗有力,确实有一处不大显眼的残缺。“这……赔偿了多少钱?”我好奇。“哎呀,妹妹,那会儿的打工仔是没有人管的。管了吃住和医药费,他还要怪你耽误了工作进度。”他失笑,口吻像是在说一个过去了很久的无关紧要的事。这样一耽误,入场已经停止了,但距离闭馆还有好一段时间。文伟只好在外面等着另外两个女员工出来。在闷热的小板房,老板娘打趣我,年龄不小了,该抓点紧找人结婚了。我摆摆手,脸色不好看——过年到现在,已经被身边人催婚到麻木了。文伟听了,却说:“缘分这个事情慢慢来,结婚也不一定就是好事。”老板娘笑了。他诚恳地看着我:“自己喜欢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,人生嘛,有很多种活法”。在时稀时挤的人流中,他跟我们说起了自己的人生和那盘仍在苟延残喘的生意。2020年,文伟的女儿满13岁,正好跟他辍学打工的年纪一样。他感到惊心,不敢想象女儿的心境和状态——她显然还是个孩子,平时还会撒娇。但13岁时的文伟,早就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。1998年,因为家里贫穷,无人管教,加上自己无心学习,个头不到1米5的他,已经烧过红砖、摘过枸杞叶、进过罐头厂。在工地搬运搭脚手架的钢管,一条钢管6米长,重三四十斤,扛上肩,他的世界变得摇摇晃晃。工人间有一个口号,叫做“吃三睡五干十六”——比现在的996还要辛苦。他和大人干着一样的粗重活,拿一样的钱——每天12元。后来因为一包假饼干,他食物中毒,一天流了七八次鼻血,床都濡湿了。工头害怕出事,二话不说就给他撵走了。来来去去的打工经历,一样悲惨、辛苦。在上有管理层严苛的压迫,在厂与厂、活儿与活儿、城与城之间,还充满了卑鄙的专门对农民工下手的骗局。他上过不少当,电话卡、车票、传销,每一次都要丢掉半个月或更多的工资。青少年时期因为吃不饱,过度劳作,他的血压低过90,常常站不稳,勉强长到1米6后,再也没有长过个子。千禧年后,文伟来了广东。那7年里,文伟学过修车,进过鞋厂、家具厂。熬到2007年,他凭着好技术被客家地区一家小厂的老板挖去做了车间主任。老板在他一人之上,器重他,一个月工资给3000块钱。他有了自己的小灶,外出厂里还有配车,只要厂不倒闭,未来似乎终于可以稳当下来。这年年底,女儿在老家出生了,文伟与女友奉子成婚。孩子的忽然到来,改变了他原本平淡打工、漂泊异地、一眼看得到头的未来。他想离家近一些,陪着孩子长大,于是辞了职,决心回老家。最开始,他去了苏州——在广东学的那一套在这里用不上,“像个二傻子一样”徘徊了十多天,没找到工作。2008年,他从亲戚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学开塔吊机的机会,但学徒时期没有收入,妻子劝他别去,家里没钱了。他斟酌再三,还是去了,“人可能要舍弃一些眼前可以看见的利益,才可以选择更好的未来”。文伟放下了自己做过主任的身段,重新从学徒开始。汶川大地震时,文伟辛苦忙活了一天,回到宿舍碰也不敢碰电视机,妻离子散、阴阳两隔的新闻太多了。学徒期结束的第一个月,文伟得了第一份月薪,500元,全捐了出去。连饭钱都紧紧缩缩地苦熬了大半年后,文伟终于可以自己带徒弟了。有了学徒,有了人,他开始单干、做承包。做了两年包工头,文伟赚到了第一桶金,将近20万元。这笔钱加上贷款的20多万元,2010年,文伟投资了二哥开了个头、但无以为继的定制家具店,25岁的他也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,回到了家乡。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品质好、值得长期合作的家具品牌,做其当地的经销商。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品牌,厂址远在成都,他显得有些犹豫。于是,朋友推荐文伟去参加广交会,“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它们家具成品的展览”。10年前,正是建材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,全国性的建材博览会不多,高铁还没普及,规模最大的就是广东地区的广交会。广交会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家具或建材的最新样式、潮流风向,还有行业新动态和各式交流会,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。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文伟,像一个“小白”,被众多的品牌和样式开了眼界。他在人山人海的展览现场,一家一家地考察和比对后,如愿且谨慎地签下了一家家具品牌的合作,并从那时开始,一直合作到现在。这个品牌没有选错,多年来他都心存感激。后面的10年,文伟没有缺席过一次广交会。在他心里,这类博览会代表的是机会和未来。参加广交会的头几年,文伟也成了一个手提牛皮公文包、与同行互留名片的观展男人,在会场上偶尔会与搭展工人擦肩而过。他想起在东莞打工时,自己也曾多次散步走进过这样的博览会,图个好玩和开眼界,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被参展商服务的人。2013年,生意暂时有起色的文伟付完首付,在老家供下第一套房子和第一辆车子。一家人住进了商品房,妻子一边在家带孩子,一边也管着店里的杂务。次年,文伟与合伙人一同向银行贷款了80多万开了第二家家具分店,同样是主营家具定制。尽管文伟表面风光了不少,但债务一直没有清零。每个月的支出加上房贷、车贷,他就要还8万。创业对他来说,“困难太多了,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困难。生意像一个风车一样,需要不停地转,不停地转”。除了生意上的脚步不能停,家庭环境的复杂也加剧了文伟生活的困难。有了钱,也就有了更多的责任,他从最小的儿子,变成了这个脆弱家庭的顶梁柱、法官和大大小小事情的决策人。在生意场斡旋习来的情商和处理能力,在简单繁琐的家庭关系里,却变得消极和无能。大哥一直留在家里务农,跟大嫂一样,总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,已经离不开那片田地;二哥一辈子吊儿郎当,中年离了婚,没车也没房,大多情况下靠文伟接济过日;基本算是文伟一手带大的妹妹,在2010年意外怀孕后,患上了需要终生治疗的1型糖尿病,文伟承担起了其所有的治疗费用;母亲则一辈子穷惯了,小气难缠,有些专横独断,常常给他要气出血病来,婆媳关系一直不好,好几次,他都看见妻子一边洗衣服一边哭。文伟渴望在自己的小家里得到安宁,却求不得。一则文伟对自己家人的接济,让妻子一直很有意见;再则,妻子和他结婚时年龄也才20岁出头,还是孩子心态,性情懒散,也不会做饭,平日连孩子也是文伟看顾得多。文伟当时想,原来赚到了钱,生活的问题并不会减少,但又转而一想:“也许只是钱还赚得不够多?”于是他对自己生意更加上心。小城的生活是安逸的,但生意的流水一直不上不下。从2015年开始,城里的家具店多了起来,文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。同一时间,随着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,买房子来供自己住的人口在下降,搞装修和置家具时人们大多挑选最基础和最便宜的,文伟和同行们都意识到了,对目标客户群体大多为小康人群的家具店而言,生意开始走下坡路。那些年,文伟日夜像个不会停歇的陀螺一样围着生活转。生意之外,一直住在文伟家里帮着他妻子带孩子的妹妹陷入了严重抑郁,加上糖尿病的病情,文伟不得不频繁出没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从此染上了医院的阴郁气息;二哥冷不丁地谈了个年轻女友,不光将给前妻的抚养费停了,还时常让文伟为他与女友幽会的交通、住宿费买单,文伟还不得不代替二哥,时常飞去侄子的城市看望,不让侄子感觉到被父亲这边的家庭所遗弃;女儿上的私立小学,一年光学费就要2万多,还报了不少名师的补课班,花费居高不下——这样一来,真正能存下的钱并没想象的多,妻子常问他:“你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?”为此两人的争执越来越多,体己话越来越少,关系也越发冷淡。2017年,国家出台《建筑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,新建住宅全装修将成为未来的趋势。各地政策不一,江苏省出台政策,要求到2020年一半以上新房以成品房交付。这的确是建筑行业的革新,也有利于生态环境,杜绝资源浪费。但作为建材行业的个体商户的文伟,已经预料自己的生意在未来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。那段时间,文伟在广交会上听了一场建材行业的网络电商经营模式的分享会,惊觉传统模式无疑将被淘汰,而电商这种全新玩法他完全不得要领,身边也没有人才来开拓,更没有余钱去探索。再三考虑后,2019年年初,文伟决定从利润少的低端市场进军利润有保障的高端市场,决心升级店铺的档次,打造好口碑和好服务,为更多相对富裕的客户群体服务。这年8月,他在一个好地段的商场盘下了一个新店面,因为资金紧缺,还没来得及好好装修。他盘算着,年末资金一回流,就把这个代表未来的店铺好好装修一下,好大干一场。准备2020年大干一场的文伟,在疫情面前,只能缴械投降——像是水断流了,跟客户和重要人物的关系,因为没有走动,静止了。客户被疫情冲刷走了,说好的成交单没了下文。一年租金60万,整个堆满货物的厂房静悄悄。20多个员工无班可上,工资还是照给。出于疫情平稳后再赚钱的野心,也因为闲得慌、客流量零星,文伟觉得这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好时机。3月份,文伟用了30万元来装修了年前盘下的面对高端市场的店铺。后来证明,这个决策让他之后手上可以周转的资金少了一大半。平静下好似无事发生,但工厂的数据说明了一切:此前店铺一个月的成交额在100到300万间,疫情这几个月,最好的成绩是一个月成交了将近20万。这场战役还在拉长战线,他并不特殊,挫败和绝望蔓延覆盖了他整个做生意的圈子。他不是最受挫的那一拨商家,不是娱乐业,也不是餐饮。他身边有个大哥,年前耗资巨款试营业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洗浴中心,没撑到正式开业就倒闭了,亏损近千万;还有好几个开餐饮的朋友,几个月没有开过单,食材全部放到发霉或变馊,两三百万亏损下,纷纷闭店;他还在都市新闻里看到一则故事:有一个失业的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喝上奶粉,不惜上街抢劫。他形容自己只是一片巨大无边的沙漠里的一颗沙子。而在这个危机下,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都会让情况再恶劣百倍。混乱和亏损之中,家庭乱战四起,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争吵。妻子埋怨文伟装修店铺的决策,还要求更多的钱贴补娘家。文伟埋怨妻子过年时过于阔绰地花钱,提出想要变卖金饰来度过危机。一开始两人的争吵总是跟钱相关,到后来,是价值观和鸡毛蒜皮的生活方式。有一次,两人甚至为了开会的一次迟到而争得面红耳赤。“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,我也累了。”4月底,文伟离婚了,成了“疫情离婚潮”中的一员。妻子提出离婚时,两人正相对无言地吃饭。他没有吃惊,只是握筷子的手抖了一下。他没有苦心挽留,感到有心无力。在饭桌上,他点了点头,说,好。他想,这样一个不快乐的家庭,解放她,也放过自己。他们决定好聚好散。财产分割上,文伟只给自己留下了一辆车和公司,其他都给了妻子,包括3套房子、孩子的抚养权,他们没有争,女儿跟谁都行。表面上是一场和平分手,但文伟为此喝了好多顿酒,才签下离婚协议书。“从孩子角度来考虑,不会有比原生家庭更好的组合。”他伤透了心,决定不会再婚。离婚一事,家里人没有插手和劝合。不过一家人都有共识,暂且瞒着女儿。前妻还如常地住在家中,文伟则在自己的店里辟出了一个睡觉的空间。5月,文伟重情义的性格,让他在这场危机里又陷入一个新的深坑。一个朋友经他好心介绍,接下了一个面铺,干了10天,没赚到钱说要退出。周旋争执了许久,文伟作为介绍人,觉得不好意思,便将这个烫手山芋接了过来。做生意这么久,约谈价格这件事他总是很不擅长。不知是否因为做了10年工人的缘故,赚别人的钱对他来说,隐隐约约有一种亏心感。这一次,面铺谈价格时,他不光填了朋友投进去的所有钱,还一口答应了别人年前租金的价格。面铺接过来这么久,对他来说,只是账面上每个月又多开支了的3万块钱。在一些黑暗的时刻,他会萌生一种逃避的心态,期待这个店可以让他从生意圈子中跳脱出来,不用再周旋社交,只需要做简单的饮食。市场一直到夏季还没有明显的回春迹象,生意圈的人纷纷意识到这是一场余波还将持续很久的危机。到了7月,文伟保守估计自己已经损失两三百万,但更多的损失还无法确定。他变得更加心灰意冷:“我更确信了一件事,我其实不适合做生意。” 对万千中小型个体商人来说,这是一场走钢丝的战争,走不走结局有可能是一样的,但往前走才有可能闯关成功。大部分人愿意这样相信,文伟是其中一个。在他们生意圈子有一个说法:人一旦倒下去了,就很难再翻身了。他需要二三百万来渡过危机。存款很快用完了,因为名下没有房产,他很难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。他只好去拆借,借高利贷,找朋友借钱,拆东墙补西墙。大多数身边人的状态几乎跟他一样,没有余钱,还要向外借款。3万、5万、50万,聚沙成塔,最高的一份利息,一个月10万块钱要还4千元。窟窿随时间的拉长越滚越大,简直像一个要一口吞了他的黑洞。文伟庆幸自己过去待人宽厚,借到了将近300万,资金注入,公司勉强转了起来。在等待市场回暖的时候,除了喝酒和独自去公园散步,文伟没有太好的释放压抑的办法。他觉得身边无人可以诉说,有时候在看网媒新闻时,他会点开评论给留言精彩的人发去私信——跟陌生人闲聊几句生活上有的没的,是他另一个几乎等同于抠手的解压办法。他不善言辞,长相也不出众,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,都没法遇到太多的理解和关注。有一天,他刷手机,刷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座上痛哭的视频——男人的生意欠债上千万,妹夫将自己的房子卖了,给他转了160万。4分多钟的视频,男人哭得像一个无助的孩子。文伟的眼睛看红了,他点开评论窗口,写了一句:“加油,大家都很难。”疫情稍微平缓后,听说建材博览会在广州如期举行,文伟早早就订了机票。文伟每次到广州,他第一怀念的是吃。每趟回来,他一定会去吃一份炒粉和叉烧饭,或者肠粉,那是当年在这里打工时的美味。第二怀念的,是那时候一起熬过来的工友们,不过他们大多已经联系不上了,广东就这样变得熟悉又陌生。这一次,他是抱着绝望中能裂出一个缝隙的期待来观展的。但他失望了,除了展览本身的种类数量和投入规模比以往要缩小好几倍外,在一系列如直播等新趋势的密集呈现下,他还看见了一种专为疫情研发出来的、足不出户也可完成家居定制的新技术。作为传统的供销商,他看到了自己迟早被挤压、被淘汰的命运。本来,他这次主要想来找一套新的五金件和灯具的供销商,结果一没有看见格外喜欢的样式,二是小厂的货也压不下去价格。参展商的生意都不比往年好,失意和疲惫的观展商们,席地在厕所门外坐成了长长的一条休息队列。匆匆忙忙的人流中,还有一些显然是外行的人,他们也来凑热闹找商机了。“今年大家的钱都花得非常慎重,走马观花来观展的人是绝大多数。”文伟观察道,“看一圈下来,人变得更绝望了。”绕完全场几圈,文伟就决定离开了。在下楼梯时,他看见二楼边沿坐着一排男人,彼此间一句话也没有,其中一个男人,正在喝绿色的罐装啤酒。聊到这里的时候,天色已经有些泛紫了,出场的人越来越多,老板娘的店铺开始挤满了人。一刻钟后,文伟的两个员工走进店铺来。他们买了3瓶冰水,两个员工的衣服被汗濡湿得紧贴背部,都结晶出盐点来了。在店铺门口,3人皱着眉头在讨论事情,讨论了将近20分钟,两个员工步伐疲惫地离开了。文伟又进来买了包烟,脸色青白,但很平静。他平淡地复述了刚刚员工们告诉他的消息:一个供货的厂家法人变更了,现在所有的货扣在原来的仓库里出不来,占营业额一半的线上店铺已经因故停运了。受此影响,有40万的流动资金用不了。他点着一根烟,一脸平淡,自言自语道:“你看,问题又来了。”他挥手向我告别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不由得心想,不知道下一个广交会还会不会再遇见他。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,并享有独家版权。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【转载】。
投稿给“人间-非虚构”写作平台,可致信:thelivings@vip.163.com,稿件一经刊用,将根据文章质量,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。
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(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、事件经过、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)的真实性,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。
其它合作、建议、故事线索,欢迎于微信后台(或邮件)联系我们。